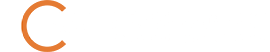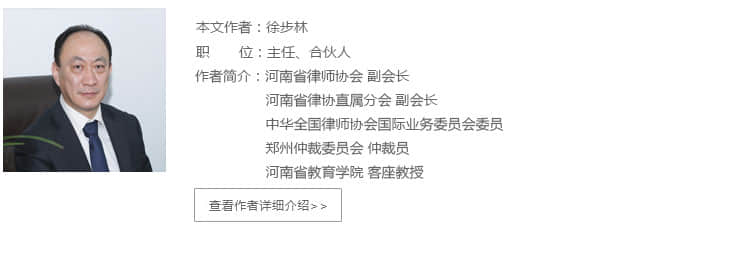律师文库
WTO和ACFTA争议解决机制的比较研究
发布时间:2015-10-29 发布人:admin
《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依托于WTO实体规则,为解决成员国之间的争端提供了可靠的程序法依据。确立WTO争端解决机制(DSM/WTO)是一个创举。除了设立争端解决机构(DSB)、保留专家组形式和增添了上诉程序之外,更具意义的是DSU通过 “否定性一致”原则、跟随执行监督机制和授权并控制报复措施等制度的建立,赋予了DSB对争端解决的强制管辖权,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裁决的执行。DSU的法律化、机制的机构化,以及程序设置的严谨性和技巧性,无不显示出WTO完整、成熟的一面,创立了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模式。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ACFTA)《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沿袭、借鉴和移植DSU的模式和规则。然而,和DSM/WTO相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DSM/ACFTA)只能算作一个雏形。从严格意义上讲,它并非一个十分健全的机制。二者在机构设置、争端处理方式的选择、执行监督和报复措施的控制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对此进行比较分析,对于ACFTA体系及其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和完善或许是有益的。
一、作为组织的WTO、ASEAN和ACFTA
从本质上看,WTO和东盟具有各自不同性质、目的和价值取向。作为一个国际经济性组织,WTO旨在为成员国提供一个谈判场所。其着眼于推动世界贸易体制进一步发展,并在实质性削减关税、贸易制裁和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性待遇等效力范围内做出努力,以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实现国际经济一体化。与WTO组织不同,东盟是一个采用松散型组织结构的区域组织,东盟成员国“在维系共同利益需要的基础上,政治经济利益,地区与国家安全利益基本一致……不干涉内政体现了东盟决策方式的特征,协商一致、互不干涉、平等对话则是这个特征的全部内涵”。[1]除了经济合作的目的,东盟还有着明显的政治一体化的倾向。因此应当赞同那些把它视为一个政治团体的见解。ACFTA是中国和东盟之间正在建设中的区域经济组织,东盟的性质和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ACFTA的决策方式和机构设置。东盟在是否应当为其争端解决机制设立更强有力的独立机构和上诉机构的问题上,已经有过多次的协商和争论,也曾表明过这方面的设想和愿望,但这样的机构一直没有建立。因此,就不难理解ACFTA迄今为何没有设立统一的、独立的常设机构的原因。
二、机构设置
建立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和DSU基础之上的DSM/WTO,在其机构化过程中设立了DSB、专家组、常设上诉机构、秘书处、仲裁员以及专家机构,等等。通过设立这些职权范围明确的机构并赋予它们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使争端解决变得可控制且富有实效。一经起诉方请求,DSB便实际享有了解决争端的强制管辖权和最终裁决权。DSU采用了“否定性一致”或称为“反向一致”的规则,即除非经协商一致决定不设立专家组,则DSB有权决定设立专家组。[2] 从而弥补了GATT1994的“肯定性一致”规则——即专家组报告必须经败诉方在内的一致同意方能获得通过——的制度性缺陷,增强了DSB的运作功效。按DSU的规定,秘书处可以向争端各方建议专家组成员的提名,在特殊情况下,总干事可以依任何一方请求,指定他认为合适的人员组成专家组。[3]在这个机制内,一旦查明已经发生了违反WTO法律规定的情况,那么启动争端解决程序所必需的利益的丧失或减损将被推定成立,除非被指控成员能够反驳这一指控。[4]此外,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还设有一个永久性的上诉机构来审查专家组的报告,制定了一整套详细的规则来保证裁决的实施,并确定由DSB直接负责对裁决、建议的监督执行和对实施报复措施的授权和控制。因此,无论是DSB对解决争端的管辖权,还是专家组、上诉机构的建议和裁决权,都显示出了强制性特征,增强了争端解决的确定性。
ACFTA争端解决框架中并没有设置类似DSB的常设机构。究其原因,这可能与ACFTA目前的松散结构有关,也与前面提到的东盟的习惯议事规则和决策方式有关。在WTO框架下,成员国让渡了部分主权,从而赋予了WTO争端解决机构在一定范围内的强制管辖权。这应当归功于WTO协定所确定的“单一承诺”原则,WTO法律是一个有46个协定组成的不可分割的共同体,需要成员国一揽子接受。然而,东盟成员国在对待部分让渡国家主权给某一国际组织的问题上好像持有相当的敏感和谨慎态度。东盟坚持和强调的是协商一致、互不干涉、平等对话的议事和决策方式。众所周知,中国、印度和缅甸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国际关系准则的最早的倡导者,而多数东南亚国家是最早的赞同者。在中国和东盟成员国中,上述方式的选择有着广泛的意识形态基础。
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中有机构安排内容,但DSM协议没有涉及机构方面的安排。法和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学方法和法学方法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殊途同归的,所谓各自的规则并非绝对的不适用于解释对方。[5] 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依托于经济的秩序化,它需要经济价值目标和法律价值目标的统一,即最大化、均衡、效率和公正、公平、正义的统一。任何一种机制如果只注重发展和推进的速度,而忽视有效的法律机制的建设,那么它运作的结果一定是有瑕疵的,也就难于达到真正意义上的高效。ACFTA《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的签订,虽然说明各方已经认识到建立法律秩序的重要性,但是机构设置上的缺失却使DSM/ACFTA难于和DSM/WTO相提并论。合理而完备的机构设置是发挥DSM功效的基础。 DSM/ACFTA没有常设机构,缺乏对裁决执行方面的监督和保障。其弊端在以后的实践中无疑会逐渐地显露出来,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高效、均衡、公平的综合目的的实现,影响到ACFTA的运作功效。
三、专家组、上诉机构、仲裁程序
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如果争端各方互相间未能通过磋商或借助第三方的帮助——比如通过斡旋、调解和调停——消除分歧,那么随着设立专家组的申请,WTO框架内正式的争端解决程序就开始了”。[6]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在获得DSB的通过后,就可以当然地被视为是DSB的建议,对争端案件的各方均有拘束力。换言之,争端各方应当按照报告中的裁决和建议执行。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解决争端中除了上述判断性作用之外,其积极作用还体现在监督有关成员执行建议和裁决方面。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认为有争议的措施与WTO法律不一致时,可以建议有关成员调整其措施并使之与WTO成立协定相符。因此,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裁判方面享有广泛的能力和权利,构成了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核心内容。WTO通过对GATT的承认、肯定和发展,确立了“诸如专家组断案等形式在内的具有司法模式性质的争端解决途径,并且在专家组断案过程中无论是证据的采信还是结论的推理都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法院化特征”。[7]DSM/WTO中的仲裁程序并非是必经程序,它作为解决争端的替代手段被纳入WTO争端解决机制之中。[8] 它是一个“解决争端的选择性辅助方法,有利于尽快解决争端双方某些明确的争议”。[9] 像几乎所有仲裁规则所规定的那样,WTO框架下仲裁程序的启动同样有赖于争端双方一致同意并达成仲裁协议,其他方的加入也需要得到诉诸仲裁的各方的同意。
ACFTA对于磋商、调停和调解给予了与DSU几乎相同的重视,但却没有采用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解决争端的模式。如果我们把磋商、斡旋、调节和调停当作政治外交手段的话,仲裁就成了ACFTA争端解决机制中唯一可选择的正式程序,而不是作为“替代手段”使用的。签署ACFTA争端解决协议,即可以被视为认可了选择仲裁的解决途径,任何一方均可以依据ACFTA《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第六条要求设立仲裁庭,而无需争端方另行协商一致、达成仲裁协议。就解决争端快捷程度而言,仲裁无疑远远优于专家组和上诉程序。问题在于,ACFTA结构中的仲裁庭是一个临时组织,其使命随裁决的做出而终结。虽然DSU中的仲裁庭也不是常设机构,但是仲裁并非DSU的核心程序。而作为唯一可选择的正式程序,仲裁的临时性给ACFTA争端解决机制的解决争端的能力和效果打了折扣。有文章建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中应当借鉴WTO的跟随执行监督制度,并且不妨由原仲裁庭代为行使跟随监督的职能。[10] 如果这样做可行的话,在尚未建立常设机构情况下,也不失为一个较为简便可行的权宜之计。
在WTO机制中,由于仲裁结果无需得到DSB的通过而只需向DSB通报,因此有人担心仲裁的法律适用会偏离WTO的规定或精神,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DSM/ACFTA中仲裁裁决也是终局性的,没有上诉的机会,以致产生了“如果因仲裁庭组成的不当或明显超越权限,裁决赖以成立的理由不清等而使裁决不公正时,那应该如何处理?”的疑虑。事实上,仲裁员通常都会审慎而充分地考虑WTO规则。如在“美国版权法案”仲裁一案中,仲裁庭指出:因为仲裁结果只须通报DSB而无需DSB通过,因此仲裁员有责任使仲裁符合WTO的规则和原则。[11] 仲裁裁决通常是终局性的,不为仲裁设置上诉程序是一种惯例性的做法。仲裁的魅力在于由仲裁员——以第三者的身份并以不偏不倚的公正角度——来判断是非,解决纠纷。争端当事国自愿将其争议交付给他们指定的仲裁员,并自愿接受裁决结果。在国际争端中,除了相信自己参与(直接地或间接地)指定的仲裁员的公正性和对法律的认识能力之外似乎别无选择。相信他们一次和相信他们两次,似乎也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四、裁决执行和报复措施
在DSM/WTO中“跟随执行监督制度”将建议与裁决的执行自始至终地置于DSB监督之下。采取报复性措施被DSB严格控制,终止减让和其他义务的范围也被明确限定在一个数额之内,这个数额须与利益损害或丧失相符。为此,DSU还设立了救济程序,如果认为报复措施违背了水平相当原则的,即可提请仲裁。所有这些设计既可以使建议和裁决得到执行并保障WTO的法律秩序得到实施,有可以兼顾到公平和均衡的原则。然而,《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定》并没有建立“跟随执行监督制度”,在“赔偿、减让或利益的中止”条款中,对于报复措施实施的水平也没有做出清晰的规定。
国际法是法律规范还是道德规范,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传统国际司法领域内的组织——无论称其为法院或是仲裁庭——在管辖权和确保裁决执行的强制力上都存在先天的缺陷。国家主权至上的观念的存在,国家尤其是经济大国对国际裁判的干预和影响始终没有间断过。执行裁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道义上的责任。WTO的最引人注目的贡献就在于,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WTO争端解决机制一方面通过对建议、裁决的执行过程的监督措施,另一方面通过授权实施贸易制裁和报复措施等方式,大大促进了裁决的执行。
通常情况下,为解决实体纠纷而设定的程序法一般应该包括两个部分:解决争议的具体工作程序(判断性部分)和裁决的效力(执行保障部分)。缺乏对执行的监督和保障,裁决的权威性就会受到挑战。对报复措施的水平缺少明确规定,可能导致权利滥用,形成新的和更大范围内的争端。这些问题的存在,势必会减弱整个机制的运作功效。DSM/ACFTA执行保障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程序问题,而是由于机构设置缺失而导致的系统性或制度性缺陷。
五、机制选择和法律适用
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WTO成员国与非WTO成员国之间的争端,选用ACFTA争端解决机制并适用ACFTA规则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如果争端双方都是WTO成员国,问题就会稍显复杂。
第一个要面临的问题是对争端机制的选择,即对程序规范的选择。在争端双方意见不一致时,就会出现DSM/ACFTA和DSM/WTO选择上的冲突。有一些文章认为:发生争端时,如果争端双方都是WTO成员,则可以协议选择WTO的或CAFTA的争端解决机制,在不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则优先适用CAFTA的争端解决机制。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至少到目前为止仍缺少法律上的依据。从本质上看,不同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是一个管辖权的冲突问题。在这一个问题上,至少WTO没有放弃管辖权的明确表示。笔者倾向认为,DSM/ACFTA和DSM/WTO之间不存在谁应当优先适用的问题。同在两个机制适用范围内的争端,应当尊重任何一方的选择。在这里也不存在协商一致的问题,争端一方既可以依据DSU的规定要求设立专家组,也可以依据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要求设立仲裁庭。在任何情况下,应该认同提出要求一方的选择。一经选择,被选择的争端解决程序就应当被启动,除非享有决定权的机构表明他不受理这一争端。
另外一个问题是解决实体争端的法律适用。从总体上看,WTO和ACFTA规则是相容的而不是对立的,而且都是开放性的。建立与运行CAFTA,除了要严格遵循WTO的有关规定等法律和规则之外,WTO和ACFTA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有文章分析认为,从本源上考察,CAFTA与WTO有相互认同性,具体表现为基本目标一致、构成主体相互重叠、CAFTA与WTO的成员都体现出高度的多样性和基本原则一致。[12]WTO和ACFTA中都没有关于法律适用的明确规定。WTO允许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并不导致区域经济组织(包括自由贸易区)的法律性文件、成员间的协议都能够当然地成为WTO法的特别法。在ACFTA法和WTO法就某一问题的规定有冲突的情况下,WTO明确认可的范围内的规定可以作为特别法优先适用,例如特惠待遇和零关税问题;如果超出WTO明确认可的范围,或违背了WTO的基本原则,则应适用WTO法。按ACFTA争端解决机制协议规定,若争端双方未能就仲裁庭主席人选达成一致,则应请求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来指定仲裁庭主席,争端各方应接受此种指定。[13]这一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ACFTA和WTO的关系。在ACFTA机制中请求WTO总干事指定仲裁庭主席,也许更有助于在断案中协调WTO和ACFTA规则的适用。
为了保证规则的稳定性和覆盖面,WTO规则和ACFTA规则在用语上是相当模糊的。因此,在对规则做出解释和对实体问题进行判断的时候,考虑和引用国际判例是必要的。WTO争端解决的实践中,对其他国际条约、习惯国际法和判例的引用是很常见的。WTO专家组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我们认为那种声称第7条第1款意味着在合理解释专家组面对的诉讼请求时不能援引习惯国际法的主张是没有依据的”。[14] 同为国际公法的分支,作为WTO框架下的区域经济组织,ACFTA不应当排斥对WTO规则和国际法判例的引用。
六、结语
DSU被纳入到整个WTO捆绑协议之中,其囊括了几乎所有的解决争端的程序规定,改变了GATT1947时代争端解决程序规定过于分散和互不协调的状况。DSM/WTO有着复杂而完善的机构设置——不但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DSB等常设的和非常设的机构,也包括一些诸如《装船前检验协议》中的“独立机构” 的特殊机构,在程序规定方面也达到了颇为完善的程度。它的存在为建立DSM/ACFTA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全面承袭DSM/WTO的规定,又导致了DSM/ACFTA效率和作用上的不确定性。
DSM/WTO在解决争端中所发挥的作用不断地被实践所证实。那么,新生的、发展中的DSM/ACFTA的作用将如何呢?相信时间会做出回答。
参考文献:
1、D. J. Harris, Cases and Materials on International Law, 1998, London Sweet & Maxwell, 5 Ed.
2、黄懿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法制论坛”,www.cel.cn , 2004年4月9日
3、Hank Lim and Matthew Walls,ASEAN after AFTA: What’s Next?,Dialogue & Cooperation,03/2004
4、江必新,《WTO与司法审查》,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第1版
5、刘筱君、邓光娅,《中国——东盟FTA的机制建设》,《商场现代化》,2005年第3期
6、李双元等主编,《世贸组织规则研究的理论与案例》,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第1版
7、M Matsushita, T J Schoenbaum & P C Mavroidi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aw, Practice, and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8、P-T 施托尔、F 朔尔科普夫著,南京大学中德法学研究所译,《世界贸易制度和世界贸易法》,法律出版社,2004,第一版
9、R. James Ferguson, ASEAN Plus? the Drivers of Open Regionalism-Australia and the Asia-Pacific, www.international-relations.com, 2005,
10、R 考特、T 尤伦著,张军等译,《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新一版
11、王受业,《东盟未来发展趋势及出路》,《外国问题研究》,1999年,第4期
12、杨国华等,《WTO争端解决程序详解》,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第1版
13、杨丽艳、蒋得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规则新发展——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的法律问题》,www.chinalawassociation.com,2005年8月19日
14、周文贵、陈龙江,《论CAFTA与WTO的相互认同性》,《南方经济》,2005年第7期
15、Korea-Measures Affecting Government Procurement WT/DS163/R, Para.7.96.
16、United States – Section 110(5) of the US Copyright Act, WT/DS160/ARB25/1, 9. 11. 2001
17、Turkey – Restrictions on Imports of Textiles and Clothing Products, WT/DS34/R, 31. 5. 1999; WT/DS34/AB/R, 22 October 1999; adopted on 19 November 2000
[1] 王受业,《东盟未来发展趋势及出路》,《外国问题研究》,1999年,第4期
[2] DSU,第6条
[3] DSU,第8条
[4] DSU第3条第8款
[5] R 考特、T 尤伦著,张军等译,《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新一版, P 9-25
[6] P-T 施托尔、F 朔尔科普夫著,南京大学中德法学研究所译,《世界贸易制度和世界贸易法》,法律出版社,2004,第一版,P 172
[7] 李双元等主编,《世贸组织规则研究的理论与案例》,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第1版,P 621
[8] DSU 第25条
[9] 江必新,《WTO与司法审查》,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第1版,P 82
[10] 杨丽艳、蒋得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规则新发展——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的法律问题》, www.chinalawassociation.com , 2005年8月19日
[11] United States – Section 110(5) of the US Copyright Act, WT/DS160/ARB25/1, 9 Nov. 2001。参见:杨国华等,《WTO争端解决程序详解》,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第1版
[12] 周文贵、陈龙江,《论CAFTA与WTO的相互认同性》,《南方经济》,2005年第7期
[13] ACFTA争端解决协议,7. 3
[14] Korea-Measures Affecting Government Procurement WT/DS163/R, Para.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