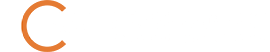一、通道业务的概念与特征
作者:严林
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河南昌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任何形式之法律意见或建议。如您有意就相关话题进一步交流或探讨,欢迎与本所联系。
信托通道业务即信托公司设立信托计划作为通道,银行负责资金端的募集和资产端的投资指定,借助信托计划实现银行资金出表、规避监管指标约束等目的。纵观立法层面,关于“通道业务”的概念尚未存在权威定义,仅列举部分规范中的描述如下:
1.《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商业银行并表管理与监管指引的通知》(银监发〔2014〕54号) 第87条规定,本指引所称跨业通道业务,是指商业银行或银行集团内各附属机构作为委托人,以理财、委托贷款等代理资金或者利用自有资金,借助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等银行集团内部或者外部第三方受托人作为通道,设立一层或多层资产管理计划、信托产品等投资产品,从而为委托人的目标客户进行融资或对其他资产进行投资的交易安排。在上述交易中,委托人实质性承担上述活动中所产生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等。
2.《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银监发〔2017〕55号) 第一条规定,本通知所指银信通道业务,是指在银信类业务中,商业银行作为委托人设立资金信托或财产权信托,信托公司仅作为通道,信托资金或信托资产的管理、运用和处分均由委托人决定,风险管理责任和因管理不当导致的风险损失全部由委托人承担的行为。
3.《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93条关于“通道业务的效力”中规定,当事人在信托文件中约定,委托人自主决定信托设立、信托财产运用对象、信托财产管理运用处分方式等事宜,自行承担信托资产的风险管理责任和相应风险损失,受托人仅提供必要的事务协助或者服务,不承担主动管理职责的,应当认定为通道业务。
综上,可将通道业务的特征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委托人自主决定信托设立、信托财产的运用对象、信托财产管理运用处分方式等事宜;二是委托人自行承担信托风险;三是受托人仅提供必要的事务协助或者服务,不承担信托财产管理职责。
二、通道业务的监管规范及效力争议
对于通道业务的效力,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所规定的信托均为主动管理信托,并不存在事务管理类信托或者将通道业务认定为信托业务的问题。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三十条关于“受托人应当自己处理信托事务,但信托文件另有固定或者有不得已的事由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处理。受托人依法将信托事务委托他人代理的,应当对他人处理信托事务的行为承担责任”的规定,按其规范意义,在信托设立后,受托人即便委托他人代为处理相关事务,对于信托财产的尽职调查、管理运用、收益分配等仍需承担责任。结合实践中通道业务的开展,绝大多数为了在追逐高额利润的同时能够规避监管政策,达到表面合规的目的,故此应当以目的违法为由认定其无效。另一种观点认为,应立足于现实经济生活的发展,通道业务作为事务管理信托有其存在的空间,对其效力不能一概予以否定,而应配合监管政策,逐步加以规范。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号,下称《资管新规》)第二十二条规定:“金融机构不得为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产品提供规避投资范围、杠杆约束等监管要求的通道服务”。同时在第二十九条中明确“本意见实施后,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在本意见框架内研究指定配套细则,配套细则之间应当相互衔接,避免产生新的监管套利和不公平竞争。按照‘新老划断’原则设置过渡期,确保平稳过渡。过渡期为本意见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底。过渡期结束后,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产品按照本意见进行全面规范(因子公司尚未成立而达不到第三方独立托管要求的情形除外),金融机构不得再发行或从存续违反本意见规定的资产管理产品。”因此,可以看出《资管新规》已明确禁止规避监管类的通道业务。
此外,关于政策监管层面的禁止态度是否构成影响效力判定的因素,一则区分该规定系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范,二则是否可借道“社会公共利益”或“公序良俗原则”来认定其效力。
三、涉及通道业务之信托合同效力判定
关于涉及通道业务的信托合同效力的判定,需遵循《资管新规》中“新老划断”的原则。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93条关于“在过渡期内,对通道业务中存在的利用信托通道掩盖风险,规避资金投向、资产分类、拨备计提和资本占用等监管规定,或者通过信托通道将表内资产虚假出表等信托业务,如果不存在其他无效事由,一方以信托目的违法违规为由请求确认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依据信托文件的约定加以确定”的规定,可以看出在过渡期内仅以通道业务涉及信托目的违法为由,并不会直接导致信托合同无效。
针对存量通道安排合同效力的司法认定,2018年4月27日《资管新规》发布后,最高院于2018年6月29日在2015民二终字第401号案中作出回应,最高院认为“(本案所涉信托贷款通道安排)发生在2011年,属上述金融监管政策实施前的存量银信通道业务。对于此类存量业务,《资管新规》第二十九条规定按照“新老划断”原则设置过渡期,过渡期设至2020年底,确保平稳过渡。据此,案涉《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和《信托资金借款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北大高科公司有关合同无效的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但也存在类似司法判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认定信托合同无效的情况。比如在(2018)沪74民终120号案中,上海金融法院认为“2015年4月22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中国证监会通报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开展情况》,该文明确“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场外股票配资、伞形信托等活动,不得为场外股票配资、伞形信托提供数据端口等服务或便利”。该规定虽然并非行政法规,并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无效情形,但其目的在于在2015年特定股市背景下,通过规制场外股票配资、伞形信托的融资融券业务控制金融市场风险,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此种强监管背景下,双方当事人仍签订以伞形信托加杠杆形式的对外投资为目的的《委托投资管理协议》,属于违反社会公共经济秩序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应属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信托无效:(一)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二)信托财产不能确定;(三)委托人以非法财产或者本法规定不得设立信托的财产设立信托;(四)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信托;(五)受益人或者受益人范围不能确定;(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笔者认为,《资管新规》并非行政法规,相关规定原则上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在相关配套细则尚未出台、不符合监管要求的标准尚未确定的情况下,若信托合同的签订、履行不存在法定合同无效及上述信托无效事由,即便过渡期已经结束,亦不可仅因涉及通道业务而直接否定信托合同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