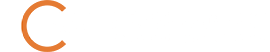网络直播产业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发展而兴起,同时也带来了直播冲动打赏与高额打赏等问题。未成年人高额打赏事件频发,给社会和家庭造成了不良影响,亦对司法实务提出了挑战。网络直播打赏产生之初,其法律性质就备受争议。从网络直播打赏行为的自愿性和非对价性等特点分析,其中所涉法律关系更近似于赠与合同。鉴于未成年人的心智不成熟,会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对于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行为的效力和是否能够被撤销的问题,应予以综合考虑。
关键词:网络直播;打赏;法律性质;民事行为能力
一、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行为的法律性质
对法律关系的定性不同,适用解决纠纷的法律则相应不同,其产生的法律后果也不一样。在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发生纠纷时,涉及的法律关系还存在着比较大争议。目前来说,对于打赏行为的性质认定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赠与合同关系
根据《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打赏应认定为网络主播与用户之间达成了赠与合同,赠与人是网络直播平台的打赏用户,受赠人是在网络直播平台进行表演的网络主播。用户在网络直播平台进行注册并充值兑换虚拟礼物后,可以对自己欣赏的主播进行打赏。当事人的打赏行为是对网络主播表演或人格魅力的一种认可,从而进行无偿赠与的行为。主播开通接受打赏的服务亦体现了本人接受他人打赏行为的意思表示,接受赠与后的行为也完全是凭主观意愿进行互动。基于赠与合同的诺成性质,双方在观众发送“打赏”按键后就构成意思表示的合意,赠与合同即成立。
(二)服务合同关系
此种观点认为,所谓服务合同,就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以劳务为债务内容的合同。在网络直播中,直播表演就是网络主播提供的劳务,而打赏行为则是购买劳务服务。但是,这种对价的支付并非强制性的。从当前的网络直播商业模式来看,用户进入直播间可以免费观看直播,而后决定是否打赏。直播打赏是一种对价权掌握在观众手中的交易模式。
本人认为在网络直播平台的打赏行为更接近于赠与。首先,打赏行为具有非强制性和随机性。其次,打赏行为具有非对价性,其符合无偿性的特征,打赏金额的差异完全折射出个人情感的表达,应充分考虑到打赏用户的初衷是对主播的欣赏与支持,其主观意向更多倾向于赠与。最后,赠与合同中以财产的终局转移为目的,在网络直播打赏形成的法律关系中,合同内容更注重用户财产的转移,对所谓表演或服务并不要求达到相应的标准或有某种交易上的规制。综上,网络直播打赏行为更类似于赠与。
二、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行为法律效力
我国《民法典》第144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该法第145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根据上述规定,在未成年人充值打赏的具体争议中,未成年人对于某一民事法律行为来说,是否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主要取决于未成年人的实际年龄、支付的金额、是否经过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追认等因素。此外,在诉讼的过程中,往往还存在着交易主体认定的证明难题。由于无行为能力人从事民事行为一概无效,故后文主要讨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充值打赏效力问题。
(一)交易主体的认定问题
在网络直播中,无论是充值还是打赏,电子系统的交易环节都不得不面临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交易主体的认定。在网络环境下,尤其是在非实名制的状态下,单纯凭借一个用户观看直播的内容与消费的习惯很难辨别他的年龄。即使是在实名制的情况下,也无法避免未成年人使用家长身份证注册账号,并将家长的支付宝、微信、银行卡等与账号绑定,继而进行消费。因此,在认定未成年人直播打赏的行为能力时,首先需要未成年人一方举证使用直播账号的主体是未成
年人,而非账号的注册者。
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由于原告依据未成年人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来要求法院认定充值、赠与无效,继而主张直播平台与主播返还财产,因此,相应民事行为能力不足属于使合同归于效力待定或无效的事由,应由提出者也就是原告进行举证。
从目前的案例实践来看,有以下几种证据可以作为参考。第一,直播账号的实际控制。未成年人使用直播账号以及支付账号,都会熟知直播账号名称以及支付所用的银行卡、支付宝账号的密码。而且,在账号注册时用户也可能会设置找回密码问题。通过问题的答案也能够确定账号注册时当事人的身份。账号、密码与找回密码的问题都是直播账号实际归谁控制或使用的用力证明。此外,未成年人是否能够熟练操作直播账号也可作为直播账号使用情况的参考。第二,用户的行为分析。用户的行为包含用户打赏、充值发生的时间、频率。第三,当事人陈述。当事人陈述作为一种法定证据,能够反映法定代理人与未成年人之间的关系、未成年人对直播行为的认知,以及法定代理人是否使用过直播账号。在与其他证据相结合的情况下,当事人陈述可以作为判断直播账号的真实使用者的证据。
(二)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
1.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充值打赏行为是否与其智力相适应的证明问题
(1)如何认定充值打赏行为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智力相适应《民法典》第22条规定:“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如何界定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不仅是立法的难点,也是目前网络直播行业的实际困难。我国司法实践一般是从认识力、理解力、辨识力等方面加以分析,看未成年人能否认识法律行为的性质、理解其内容与后果,并对相关交易风险有所辨识。
在网络直播中,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对所实施的充值、打赏行为是否具有相应行为能力,应当从未成年人是否对消费的价值有明确的认识,可从充值和打赏的数额、未成年人的经常居所地、家庭经济状况、消费习惯等角度综合分析。
(2)是否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的认定
网络直播中未成年人巨额充值、打赏的行为若引起纠纷,通常意味着法定代理人往往都不会追认行为的效力。那么,在何种情形下可以认为法定代理人同意未成年人实施巨额充值、打赏的行为呢?在现代信息社会,身份信息、资金账户信息、交易密码等是网络交易中最为重要的个人信息,自然人对这些信息负有妥善保管义务,一旦由于自身原因而泄露,需要自担风险。当法定代理人允许未成年人使用相关信息注册直播账号或使用银行账户消费时,却不添加消费限额等限制措施时,其就应知道未成年人可能利用该信息进行网络交易。这种明知风险而为的行为,可以看作法定代理人对未成年人大额充值、打赏的默认。
实践中还存在未成年人趁父母不备,偷拿手机与银行卡进行消费的行为。此时,需要父母具体举证自己是否尽到妥善保管手机与银行卡的义务,以及是否曾同意未成年人的巨额消费。法定代理人可以通过证明自己事先并不知情、事后也激烈反对等事实表明自己的态度(例如举证证明孩子下载软件时自己在外地、自己对此种活动一贯的态度、事情爆发后短期内与孩子的聊天记录、所采取的措施等)。
三、未成年人充值打赏行为被撤销或无效后的法律责任
若认定未成年人在充值、打赏时不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那么未成年人有权根据《民法典》第157条请求平台和主播返还已经支付的款项,请求的对象可根据具体情况不同而进行分类,详述如下。
在充值、打赏行为被认定无效后,交易相对方平台与主播负有返还财产的义务。实践中主播与平台之间存在不同的合作模式,可能是服务合同关系、合作关系或劳动关系等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在讨论具体承担返还财产义务的主体时,需要区分不同的情形加以讨论。在直播平台与主播构成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主播基于其与平台之间的劳动合同进行的直播、接受打赏等行为均构成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均由平台承受,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直接请求平台返还充值与打赏的相应金额即可。若主播与平台之间是服务合同等其他关系,如前所述,若未成年人用户充值后对主播打赏,那么应当同时起诉直播平台和主播,分别要求直播平台返还仍然剩余的充值金额,以及要求主播返还已经赠与的代币金额。
四、未成年人网络直播打赏的救济途径
首先,家庭教育是避免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的第一道防线。根据《民法典》第26条第1款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促使子女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其次,直播平台与主播作为未成年人消费者充值、打赏的相对方,应当承担相应的保护未成年人的注意义务。
再次,直播平台需要建立完善的主播管理机制。一方面,平台需要对主播资格进行审查,并在主播开播时进行与未成年人交易相关注意事项的培训。另一方面,平台应对主播劝诱未成年人消费的行为进行监管或设置惩罚机制。
最后,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方面的相关立法并不完善。虽然《民法典》中对未成年人法律行为效力作出规定,但是仅依靠事后司法救济不足以形成有力保护未成年人的良好业态。应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消费行为以及各方义务进行规定,同时建立完善的行政监管制度,从网络服务产品设计到实际运行进行日常监管。直播行业也应当积极出具行业准则与相关规范,实现自我监督与规制。